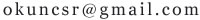简析十七年时期革命小说特点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期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突出点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地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如:和平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等。谈到英雄在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却是盲目的崇拜,而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英雄,却是一个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而中国《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生活的隐匿,除了众多作家本身就是乡土作家以外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近代城市被认为是“罪恶的渊土”,及资产阶级道德和社会腐败产生的场所,再者都市文学本身就具有消费、娱乐的腐蚀性特征在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的。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城市的隐匿,使得“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所表达的现代化诉求缺少精神、物质基础的构建,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十七年文学”似乎成了红色中国、乡土中国的书写。城市的隐匿,对“十七年”城市题材文学作品艺术内容的改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表现在“十七年文学”日渐取消了城市生活中礼俗的审美意义,而礼俗作为一种文化复合体,正体现出城乡生活的差异性。城市生活有着较乡村生活远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活形式,对它们的应对是城里人对自己心智的考验,世故的城里人常常在一些巧妙的应对中体会着生活的惬意。日常生活好似波澜不惊的小溪,缓缓覆盖人的生命,小市民们的世故、圆滑保护了他们,养成了他们生命力的内敛。在日常礼俗场景中,广大市民人性的内容徐徐展现,其背后的文化结构呈现了出来。虽然这种文化结构多是固态的,有很大的惰性,但即使是对它的批判也得建立在对它的呈现的基础之上。正如老舍,他的京味追求“是以对于北京的文化批判为思考起点的”,虽然他的作品因多顾及京味而被指缺少勃发的生机,这正是老舍的小说需发展的地方,而这发展并不能简单化为剥离日常生活。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乏新、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中途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十七年文学”语境将对日常生活的疏离推到了极端,连日常生活中人生存所依赖的最基本的关系——爱情和亲情都遭到排斥。爱情和亲情本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创作的母题,但在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作家们创作的禁区。
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如果要“断代”的话应该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第一阶段应该就是“十七年文学”;第二阶段应该是“文革文学”(如果当时还有文学的话);第三阶段是“伤痕文学”;第四阶段是九十年代至今。
我认为这十年的历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不应该简单的把它界定为“高度相似性”的文学时期。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当然,我也不否认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现代文学的作品是最丰富和最具艺术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艺术大家,例如鲁迅、矛盾、郭末若、巴金、冰心、郁达夫、老舍、丁玲、徐志摩等等。
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暴风骤雨〉等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郭沫若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但我觉得“十七年文学”比“伤痕文学”要从容、平静、丰富,比“今天文学”要高尚、积极(“今天文学”在我看来就是“床上文学”、“赚钱文学”、“没落文学”。
***************************************************************
十七年小说之我见
——浅谈人物形象的英雄典型化
"十七年",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当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忽略它在文学史上的漫长——即使已经沉淀了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是"活化石":那就是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那时的文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唯独感受不到写作主体的存在。极端外向的文学是不允许创作者以及被创作者保留个人的秘密的,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便突出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
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的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此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用来平衡随战争时代消逝反而逐渐积累的焦虑感——因对历史英雄丰功伟绩的反复景仰与重构中产生的"生不逢时"的焦虑感——的和平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等。
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在中国这种心理显得更有代表性:被救的心态已经成为国名性格的一部分(在价值观念混乱的今天,这种心理现象似乎有增无减)。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和俄底修斯,两人都是战争英雄,但一个是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另一个是智谋过人且沉着的参谋,而后者的英雄的人性却被政治过滤得过于纯净致使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废除了与阶级性无多大关系的个人情感内省,例如《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今天的作文教育就是从"黑白分明"开始的,所以当获知林彪是新中国的美男子之一的时候,那种惊讶是很多学生体验过的)。
******************************************************************
十七年文学
更重要的一点是:英雄不死,他们无论能耐多大,都是由一种带有光环的无形神圣力量赐予的,所以英雄的存在也是无条件地奉献给它的。由此,英雄不死的模式实质上具有了某种仪式的效果:象征着一种信仰的永存不灭。至此也就表明,中国的英雄在成其为英雄的同时,也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同时,在这种创作观念的指导下,文学的永恒主题、为人最重要的构成内容之一——爱情,在十七年小说中几成绝响。爱情具有精神与肉体对立统一的复杂性,革命的理性又如何能区分得清?这个错误百出的历史阶段对爱情的拒绝非常彻底,甚至还不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革命加恋爱的普罗文学。《秋娥》中金田和秋娥的婚姻得以维持,不是"情"的催化,二十政治上的共同进步;《革命夫妻》中阎新生病态地排斥夫妻间正常的情感,将"儿女情长"视为洪水猛兽;《红岩》中江姐和老彭的爱情充满了革命内容,而没有任何一丝男女间的情与欲;......爱情在英雄身上无一例外的"缺场",暗示了其存在完整性和真实性的一种危机,在后代思想相对解禁的读者看来,只能是一些空洞的载体符号。
十七年的小说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或者说被开了一个充满恶意的玩笑:"人"在作为"人"的文学里被"人"自身给活活地扼杀了。时代要求大合唱,小说乃至文学就只能是一个被规定了音质、音高、音域的声部而已;时代是个大系统,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就只能是一个典型的标识部分,引领人民义无反顾地忘掉自我存在的要求成为一颗齿轮与螺丝钉——在革命与建设这一巨大机器上。然虽人性在接踵而来的众多政治运动中越来越沉默,但也不说明就完全没有勇敢的非英雄化尝试。但那个畸形的年代是绝对不允许异样声音的存在的,无论多么隐讳,无论多么微乎其微。无情的批判和诘问带来的灭顶之灾不仅覆盖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自由空间,也深深的禁锢了今天所谓现代人的脚步。后辈想起"十七年"的严厉至今心有余悸,在被重整重写的历史面前裹足不前。当那些创作成果随沉重的历史流逝变得"不可承受之轻"时,它们给我们留下的更多是沉痛和悲哀,英雄身上楷模与榜样的力量打着的历史烙印一再的提醒后来的人们:十七年失去了一切,包括文学本身
回过头来,我们再从文本方面分析。不可否认,“十七年文学”有人物形象单薄、叙述语言单调、叙事策略呆滞、价值判断武断的缺陷;其间不具有发现永世不朽的经典之作,和诸如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荷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之流的文学巨匠的可能。但是,十七年繁杂的文本中却蕴含着文学史写作的有益史料。这是笔者在对十七年文学进行研究时得到的第一个认识。下面以绿原的诗歌为例进行分析,绿原的组诗《北京的时间》,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3期。第一首《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诗人抓住走在红墙外的瞬息感觉,写成了这首抒情诗。“我”走在红墙的外面,尽量走得慢一些,轻一些,一方面是倾听红墙里那颗伟大心脏的跳动,另一方面是不想去打扰红墙里的一切,因为红墙内,“一颗伟大的心脏在那里 为亿万个生命跳动着”。诗人通过对自己炽热情感的铺展,表达了对伟人的崇敬之情。另外两首则抒发了诗人对新生活由衷赞美和对美好未来无限向往的赤子情怀。这组诗没有公式概念,没有豪言壮语,在充满了浓郁抒情色彩的语言中流淌着诗人新中国成立后的激昂情感,不失为比较优秀的政治抒情诗。然而,这组诗的意义不在于它的艺术上的造诣,而在于它所蕴藏的文学史的内涵:一个对伟人如此崇拜对新生活如此热爱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诗人在此后不久的日子却被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文化体制冷落和冰冻了。一位研究过绿原的专家告诉笔者,绿原的这组诗没有收入他后来的自选诗集。这一诗作的流失,更隐含着一个文本的曲折命运和一个诗人的复杂心理。十七年中,具有这种命运的不只绿原和他的《北京的时间》,胡风和他的《时间开始了》也是类似的范例。试想,对于一个饱受了战乱和饥荒之苦的民族,一缕和平和安宁的曙光的来临,谁不充满了喜悦和希望呢?可是,这些饱含激情和富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太阳真正升起的时候,却遭遇了他们始料不及的命运。这种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其次,在十七年文学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文本。十七年的作家虽然出身不尽相同,受到的教育也参差不齐,但大都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经历过解放战争,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城市工业化建设和农村集体化运动,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所形成的人生体验曾经深深地打动过他们的心灵,成为他们永志难忘的记忆。正是这些记忆激扬他们的写作情怀,他们的人生体验也便成为具有真情实感的叙事。所谓叙事,无非是充满激情记忆的铺展和流淌。十七年小说凭着这种记忆时而对主流意识形态顺应,时而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既充斥着抹有政治色彩的御用文字,也建构出饱含生活质感的叙事话语。短篇小说《董林和小卡》对土地改革时期“中等收入者”的心态就有难能可贵的独特描述,堪称一篇佳作。《董林和小卡》发表于《湖北文艺》第2卷第6期(1950年11月号),叙述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河南舞阳某村的一对邻居,董林和小卡,自幼就非常要好。董林有六七十亩地,四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已经结婚,人手本来就多,还雇了一个帮工,闹得挺兴旺的;小卡地不多,人又少,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嫁给了董林的二儿子,日子算是撑着过。舞阳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小卡是村农会委员;董林担心自己是富农,于是开始提防小卡,小卡对董林的疏远也有些头疼。村里的地主看透了董林的心思,叫佣人到董林那里去煽风点火:共产党什么也不懂,只要有吃的就当作富农。董林吓得上了吊,要不是他儿子看见,早就没命了。地主的造谣更加厉害,村里的几个中农都慌了神。地主又给董林出主意,要董林卖掉耕牛,让麦地荒着。董林于是整天大吃大喝,也不下地劳动。土地法颁布后,董林只划一个富裕中农;他喜出望外,不仅开始下地劳动,还和小卡重归于好。小说不长,只有一千五百字左右,却一波三折地展示了中原大地土地改革时期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们微妙的心理状态。作者董伯超是一个不出名的业余作者�17�,叙述的对象不是英雄人物或者工农兵,叙述的内容也没有突出主流意识形态,所以,这篇小说发表后,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包括正面的或者反面的。但并非声名鼓噪的大家,写出来的就一律是永世不朽的杰作,也并非没有名气的业余作者,写出来的就一律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次品。从文学价值上来看,这篇并不出名的小说就要比那些名噪一时的所谓的“佳作”高出许多。此外还有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1949年9月由新华书店出版)、邵子南的短篇小说《稀罕的客人》(发表于《群众文艺》1954年创刊号)、廖伯坦的短篇小说《一封信》(发表于《长江文艺》1954年第4期)作品等都是极为有价值的叙事文本。这些文本对战争的书写,对战争所带来的苦难的书写;对新的生活的描述,对新生活中人们心理状态的描述,都是非常直观的,具有“原汁原味”的审美趣味,能够给人以内心深处的震撼。
再次,十七年文学与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联系也是我们今后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需要加以注意的一个方向。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中有一个小人物,叫朱三,文本对他的叙述不多,仅出现于《地主》和《在湖边站住脚》两章中,而且还是以次要人物的身份出现的,但他的存在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铁道游击队》中其他人物的审美形态。朱三这一载体蕴含着我们民族的某些特性,即行侠仗义,行善积德的品质。在中华民族的民间行为中,常常存在着这样一种行为方式:有能力有德行的个体,以牺牲自己的物质,甚至生命为代价,拯救处于弱势的他者,从而使自己的生存价值得以实现。知侠凭着自己的艺术直觉,捕捉到了这一闪烁着民族智慧光芒的亮点,可惜的是,知侠或许是因为某些制约,未能对这一亮点作充分的铺展和淋漓尽致的发挥。但这一民族特性在新时期的叙事文本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李锐《传说之死》中的六姑婆可以说是朱三的重塑与再现。六姑婆在父母双亡的情况下以牺牲自己的青春为代价,不仅将弟弟妹妹抚养成人,而且还培养他们读完了大学。妹妹嫁给了国民党的杨团长,弟弟却成为地下党员。弟弟被国民党逮捕将要被枪毙的时候,六姑婆冲进杨团长的家,也就是她妹妹的家,抱起杨团长的儿子,要与之同归于尽。杨团长答应六姑婆,释放了弟弟。革命成功后,弟弟所在的党分了她们家族的大宅院,杀了她们家族包括族长在内的三十余人。族长在临刑前,将他的孙子也托付给六姑婆。六姑婆抚养小孩,培养小孩读书,小孩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本市最负盛名的中学;可是,在一次运动中,小孩却被革命者扔到溪里淹死了,六姑婆在家中也自杀身亡。六姑婆和朱三一样也保存着我们民族立德成仁的秉性,正是这一独特的民族秉性使两个不同时期的叙事文本建构了同一审美价值的人物形态。一个民族的特性,是相对稳定的,也是立体多元的,它包含于政治的、艺术的、伦理的、习俗的等各个方面。稳定的多元的民族秉性保持了十七年文学与不同时期的文学剪不断理还乱的多重关联。
中国“十七年文学”(1949—1966)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直线流程的集中书写,在这“十七年”中,作家们努力想成就一个提供中国现代化方案的大文本。但由于其中隐匿了“城市”这一现代化的关键词,文本的性质变得暧昧起来。城市的隐匿使“十七年文学”文本未能展现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转型的复杂场景,略去的是人的现代生成。在审美品格上,“十七年文学”表现出对“理想”、“英雄”、“真理”、“规律”的巨大热情,在某种程度上由现实主义滑落到了古典主义。
一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从农村移向城市,要学会管理城市。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新中国的应用也促进了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从文化形态上来看,工业化带来的必将是向城市文明的转型。
城市文明取代乡村文明,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过程中文化变迁的经典模式,文学在城市文明前行中也获得了生存、拓展、繁荣的契机。且不论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的萌芽对中国白话小说创作的推动,即就“五四”新文学而言,它就是由“市民阶级”领导的。“五四”文学的现代城市文化性质,是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时期城市、乡村文明的比照,使作家对乡村的书写有了一个新的文化视角,乡村相比于城市虽有纯朴、明净的一面,但城市文明的烛照也突显了乡村封建文化的愚昧、落后和非人性,这新的视角在小说文本中具体为知识分子视角。这一视角的存在,使得作品不仅对乡土的风俗人情进行非功利的审美观照,而且文本中流露出对下层农民的深切同情,并同时批判了他们身上的文化滞后性因素。这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乡土文学作品,无论就其艺术审美性还是其文化深厚性来说,都呈现出比较高的水平,并站在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上。
这一创作视角,在赵树理的乡土小说中被置换了。赵树理自觉放弃了知识分子视角,采用农民视角,他的小说由此表现出“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今天看来,农民视角的采用使得赵树理作品的文学性受到了损害。不过他也确实由于这一视角的运用,发现了极有意味的“中间人物”,这是以往知识分子视角下的一个盲点。可惜赵树理的作品,在原“解放区”方向性的意义仅突出地表现在政治服务性功能方面,他笔下的“中间人物”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原“国统区”的作家在战争的形势下对农民群体有了新的理解,他们沿着“五四”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倒是从另一个角度深刻地切入了“中间人物”,揭示了这些苦难的人们“被奴役的精神的创伤”。1949年后原“解放区”文学唯一“合法性”地位被以政治化的行政方式确定了下来。原“国统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勉为其难地实现着创作转型,其中绝大部分由此步入创作低谷,不少作家甚至放弃了创作。特别是,60年代初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受到批判,这表明当时已经不允许表现农民滞后性因素,知识分子在城、乡比照下,对农民的文化批判就更被禁止了。“十七年”乡土文学作品中城、乡比照的视角完全被取消了。离开了“城市”的比照,乡村便失去了其特有的内涵,“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首先表现在它作为打量乡村的参照物这一角色的丧失。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
这两方面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
“十七年文学”中,当然也有个别注意呈现“城市空间”的作品,像《上海的早晨》(第一、二部)就是“十七年”城市文学中相对较好的一部。不似同类题材的作品将城市“车间”化,这部作品中非常难得地出现了“名车”、“花园洋房”、“舞厅”、“西点”等现代城市意象,作品渲染出城市富有阶层男女的颓废色彩,这是“十七年”同类题材作品中所没有的,在这一点上,它比较像茅盾的《子夜》。茅盾在《子夜》里,对都市里金钱、权力、色相所构成的巨大诱惑,以及人无力拒绝诱惑而表现出的颓废倾向,作了精彩描绘,这使得该小说虽存在着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的局限,却仍不失为一部好的城市小说。在《子夜》中作者强烈的都市文化意识成为小说中诸多城市意象的灵魂。
《上海的早晨》虽然在某些方面与《子夜》相似,但作者表现出的仍是乡村文化意识。
首先,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将乡村阶级斗争的场景简单化地位移到城市。文本中同时展开的是“城市”、“乡村”两条线索,在《子夜》里从乡下来的吴老太爷、四小姐对上海的打量构成审视都市的“他者”视角,它突显的是城市本体,但在《上海的早晨》中“乡村”的设置却不是以文化参照物为目的,而是呈现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以对应于“城市”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共同演绎旧中国将人变成鬼、新中国将鬼变成人的故事。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与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同阶段的存在物,它们并不能简单地等同起来。小说中这样的安排,恰恰说明了作者无法突破原有的价值判断体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理解资产阶级和工人的矛盾。也就是说,《上海的早晨》虽同时展开了“城”、“乡”场景,但他笔下的“城”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乡”的空间迁移而已。所以作者对城市资产阶级本质特征的挖掘,只是照搬了以往对地主阶级贪婪、自私、凶残、不择手段等特征的概括,冠之以“贪得无厌”和“唯利是图”,对资本家简单化的读解造成了小说中资本家人物形象的单薄。
其次,作者的乡村文化意识,表现在作者对城市所作的“大染缸”这一批判性说明上。
苏北干部张科长,在金钱和色相的双重诱惑下,失去了一个干部应有的操守,给国家带来了大的损失。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接管城市的干部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中确实有一部分人,无力抵挡来自极富感性色彩的城市的种种诱惑,自甘堕落。更为普遍的是类似于同一时期另一篇作品《我们夫妇之间》的情况。许多干部进城后,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物质欲望逐渐增强。建国初期人们对自己的物质欲望增强普遍地有一种罪恶感。这种罪恶感来自于想象中对自己阶级成分改变的羞耻和恐惧。《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我”,最终对自己进城后的生活方式作了否定性的反思。像张科长这样走向堕落的干部,理应受到批判甚至法律的惩处,但人们并不能由此简单地否定城市所激发起的物质欲望,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本能的渴望,只要适当地引导,便可以成为人类“向善”的一种动力。然而在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年代里,人们以实际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判别敌友关系,不恰当地将人的物质欲望视作剥削阶级的标记,要努力地对之加以克服,却忽视了它是人的现代性生成的重要基础。
从另一方面来看,对物质世界的排拒,是长期以来生活在小农经济形式中人们的当然选择,自满自足、随遇而安是小农经济形式下的一种文化心态。人们在自己种种欲望面前的罪恶感,还来源于固有的文化心态受到冲击后的不适。1949年后“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其实是远离欲望的一种间接表达,它呈现的是传统的乡村文化结构形态。《上海的早晨》中作者无意于从正面刻画一座极其感性的城市,而只是想宣告城市大染缸的特征,用来警示党的干部要洁身自好。而且在此书写过程中舞厅、饭店、“大世界”、戏院等公共娱乐场所都是腐蚀人的手段,作者对它们的否定不言而喻。
1、以长篇小说的体裁形式为最为丰富,
2、背景的高度一致性,
3、小说人物塑造的强烈‘阶级性’、‘脸谱性’”,
4、小说结构与线索的单一性,
5、小说创作具有浓重的地域特征,
6、具有新古典主义的美学特征。
简析十七年时期革命小说特点视频
相关评论:
戈耍科十七年文学的一些特征及探源 隔水观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左右同时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揭开了又一个文坛大一统局面的序幕,而五四新文化传统,如民主自由、个性化创作、独立思考等则在政权的强力控制下逐渐进入沉潜期。五四传统的沉潜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一个宣称无产者的政权建立了,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
戈耍科“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形象及其性格特点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1949—1966)的文学创作中,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一直以其独有的地位和成就而备受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当时文坛上的大多数作家都来自农村,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时,农村题材...
戈耍科欧阳山的《一代风流》三部曲:《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三家巷》作为十七年文学中独具风貌的一部作品,其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后和“”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有关家族历史还回叙至晚清),而《苦斗》则写到“大革命”失败后广州近郊震南村的农民和农场工人的生活。与《红旗谱》等长篇一样,都...
戈耍科在十七年的文学篇章中,小说的叙事艺术展现出了独特的张力和深度。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小说叙事的演变与特点。首先,我们来到革命叙事的起点。第一章阐述了革命叙事范式的建立和表达,第一节剖析了情节和人物模式的基石,如《暴风骤雨》这部作品,它的叙事张力是如何巧妙地编织情节和人物的。第二章...
戈耍科进一步地,根据小说对既定政治标准和叙事规范的遵循程度,这些故事被分类为三种叙事类型:革命叙事,明确表达了革命主题和价值观;准革命叙事,虽有所保留但基本遵循了政治导向;次革命叙事,相对偏离标准,具有更为独立的文学探索性。通过这样的分类,我们可以更深入理解十七年小说如何在叙事张力中展现其独特的...
戈耍科我总结一下 林海艺术特色如下 1、作品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表现了民主革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风云变幻的革命斗争,塑造了一批各式各样的英雄人物形象.2、史诗性追求,揭示历史本质,结构宏大,艺术虚构中加入重大历史史实,塑造英雄人物,歌颂英雄主义.英雄叙事与演义传统 “十七年”小说大多有历史叙事的倾向,这...
戈耍科关键词:十七年文学 颂歌时代 文学素材 颂歌形式 思想体现建国初期的颂歌浪潮,作为一种新的艺术规范得到很大发展,迅速成为了十七年文学乃至诗歌的主导性潮流.它的主要特点为对时代,人民,祖国和领导人民夺取胜利的党与领袖的真诚歌颂,颂歌的抒情主人公追求诗人的“自我”跟阶级,人民的“大我”相结合.十七年文学时期的...
戈耍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小说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以及革命在经历了曲折过程之后最终如何走向胜利。以对历史本质的规律性叙述,为新建立的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和真理性作出证明,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时期的民众,提供思想和生活准则。个别的 作品融入更多的个人...
戈耍科时间概念: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乏新、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
戈耍科十七年散文三大家各自的艺术特色简述如下:1、杨朔散文的艺术特色:讲究艺术构思;注重创造诗的意境;讲究艺术结构。2、秦牧散文的艺术特色:富有情趣性与幽默感;语言流利酣畅、凝练生动,采用“林中散步”和“灯下谈心”的行文作风,流露出直接面对读者的亲切感和语言氛围。3、刘白羽散文的特色:融情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