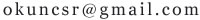张光直的往事略集
贾兰坡小时候,父母教他识字,后来又在外祖母家读过几年私塾。12岁时,母亲为了让他能受到正规教育,带他来北京找他在北京谋生的父亲。他先在汇文小学读书,又进汇文中学。1929年中学毕业,因家境困难再也没能力供他上大学了。他只好在家边自学边寻找合适的工作。1931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中国地质调查所招考练习生。他去报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分配到地质调查所领导下的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上班后,贾兰坡就被派往周口店协助裴文中先生搞发掘“北京人”工作。裴文中先生于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贾兰坡能在他手下工作十分高兴。他下决心也要像裴先生一样,做出一番成绩。1936年11月,他在11天之内连续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这次的发现,再一次轰动国内外。金灿的光环照耀在贾兰坡的头顶,迎来了他28岁的生日。1945年,贾兰坡晋升为技士(副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生代研究室划归中国科学院,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他任副研究员、标本室主任、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和周口店工作站站长。在周口店办过好几期考古训练班,他都亲自撰写讲义和授课,并进行田野实习辅导,培养了一大批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后来这些人都成了考古工作的骨干和专家。1956年,贾兰坡升为研究员。他从小小的练习生,攀登到了高层的研究领域。相继发现了比北京人时代为早的“匼河文化”、距今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距今160—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牙齿及石器、距今110—115万年前的“蓝田人”头盖骨,充分证明了贾兰坡推断的正确。贾兰坡的工作更多地转向周口店以外的地区,足迹遍及全国。特别是华北地区,投入的精力最多, 收获也最大,首先提出了中国原始文化的继承关系。他还亲自在河北、内蒙古、东北等地考查和研究后,提出中国、东北亚和北美的细石器可能起源于中国华北的论点。他的学术见解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美国学者也认为这些论点“对北美考古是指导性的意义”。1989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太平洋史前学术会议”上他曾建议把地质年代表中的最后阶段“新生代”一分为二,把上新世至现代划为“人生代”;把古新世至中新世划为新生代。高龄的贾兰坡老人不顾眼疾,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为孩子们写科普读物《爷爷的爷爷哪里来》;80岁以后他出了很多像《爷爷的爷爷从哪里来》这样的科普读物。1990年,他在《大自然探索》上发表了《人类的历史越来越延长》一文,提出了“根据目前的发现,必将在上新世距今400多万年前地层中找到最早人类遗骸和最早的工具,(人)能制造工具的历史已有400多万年了”的新论断。已经90岁高龄的贾兰坡,仍每天都在伏案工作,为他热爱的这门科学默默地奉献着。1994年年底和1995年秋,在他患有严重眼疾困难的情况下又出版了两部著作:《中国古人类大发现》(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史前的人类和文化》(与杜耀西、李作智合作,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97年10月,在他九秩之年又写完了一本“大科学家写给小读者”看的11万字的“小书”《悠长的岁月》,以总结自己的一生。书中他迫切地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人成长起来,热爱这门科学,能够接替他们老一辈的事业,运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新的学术思想,把人类起源的时间、地点等问题搞个水落石出。1995年4月他去美国参加院士会议,在旧金山为他举行的来自海湾地区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作家、记者、华人代表等一百多人参加的欢迎会上,他致答辞时说:“我虽然老了,但还希望在有生之年为这门科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1931年,当时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招收练习生,23岁的贾兰坡被录取了。这一年的5月,他来到周口店的龙骨山,在中外著名学者的指导下进行工作。龙骨山有保存完好的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堆积,地层出露状况很好。这里东南面是华北大平原,西、北面是山峦重叠的西山,山脚下有河水潺潺流过。数百年来,龙骨山一向以出产龙骨闻名,许多洞穴是原始人类理想的住所。因此,这里十分吸引中外地质和古人类学家的注意。起初,贾兰坡主要干些杂事,比如洗刷标本、整理化石、管理账目、贴制图版,事无巨细,他都做得十分认真。他同时也懂得,自己在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知识几乎等于零。所以,在每天完成本职工作之外,他就如饥似渴地找书来读。有一次,龙骨山出土了一批狼的化石,可是他却不认得。为了补课,他相约几个年轻人打了一只野狗,把吃剩的骨头制成了一具挺漂亮的标本。然后,他翻阅书籍并对照标本,将每个部位的骨骼名称一一记熟。狼和狗是同一个属的动物,他认识了狗,也就认识了狼。一天,他的导师杨钟健手拿一盒动物化石,对贾兰坡说:“你拿去鉴定一下吧,分分类。”他接过来一看,是些兽牙。他对照图版,认出了牛、羊、猪、鹿和马的牙齿。不料,当他把这些结论讲给杨教授听时,杨教授却摇摇头,要他把这些化石鉴定到“属”以下的一个单位——“种”,并要一个一个地写上标签。贾兰坡按导师的要求一一做完后,第二次送到杨教授那里,谁知又被退了回来。杨教授说:“你还得把这些动物的上、下牙齿分开,标出是第几颗牙齿。”经过贾兰坡的又一番努力工作,杨教授才满意了。俗话说:“严师出高徒。”一盒化石,三次鉴定,使贾兰坡终生难忘。他的许多考古学知识,就是这样“逼”着学到手的,从而也培养了他一丝不苟的作风。 卢沟桥头的炮声打断了周口店遗址上正在进行的发掘工作。为了保险起见,周口店遗址上发掘出来的所有化石,都保存在协和医院B楼解剖科的保险柜里。当时美国处于中立状态,协和医院还算安全。1941年,随着日美关系的紧张,协和医院的保险柜也不再“保险”。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翁文灏和胡恒德商量了好几次,有三条路可以走:“北京人”继续留在北京,妥善予以保藏;运往陪都重庆;运到美国,待战争结束后再运回北京。经过多方权衡,最终选定了第三种方案。于是,工作人员先用白棉纸包好化石,再用卫生棉和纱布裹上,包上白纸后放入小木盒内,盒内还垫上了瓦楞纸,最后分装在两个白茬木箱里。为了怕引起注意,特地不写名称,只在箱子上标了A、B字样。化石装箱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火车将其运往秦皇岛,准备搭乘“哈里森总统号”轮船运往美国。但是就在化石装车后第三天,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装载化石的火车被日军截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神秘地失踪,60年过去了,至今仍然杳无音讯。贾兰坡听到头盖骨丢了的消息后,目瞪口呆,怎么会呢?不是早都做了安排吗?从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成为贾兰坡永远的牵挂。他生前曾经说过,此生此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些“北京人”化石。贾兰坡生前,书房里有一个大夹子,专门存放着60年来他追寻“北京人”的全部资料:当年占领协和医院的日军军官的照片、日本来华寻找化石特派员的资料、中外提供线索者的来信、从四面八方收集到的真真假假的各种线索,即便是那些最荒诞不经的传闻,贾兰坡也收集了起来。贾老曾经说过:这些“北京人”标本化石,就像我的孩子,我对它们的感情是常人难以理解的。这些年来,我一直被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所折磨,我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它们找回来。在此后的岁月里,贾兰坡所做的各种努力都失败了。1999年,他和中科院14位院士联名呼吁,由于大部分知情人和当事人的辞世或年事已高,破解“北京人”头盖骨之谜愈发迫切。如果时间再拖延下去,这很可能变成一个千古之谜。贾兰坡等人在倡议书中写道:“即使它们已经毁于战火,我们也应该努力找到一个确切的下落,否则,我们将如何面对后人。”但是,天不遂人愿,贾兰坡带着永远的遗憾走了。“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成为他生前未了的一个心愿。 周口店发掘是贾兰坡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科学之路的起点——“没有周口店就没有贾兰坡”。从周口店开始,他的眼光放在人类的起源研究上。新中国成立之后,贾兰坡继续负责周口店地区的发掘工作。这位没有正式大学文凭的学者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外籍),1996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几十年来, 贾兰坡的足迹遍布全国,他的身影频频出现于丁村遗址、西侯度文化遗址、峙峪文化遗址、许家窑人遗址、蓝田人遗址等地,一生著述等身。他的研究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建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贡献,同时也奠定了他在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大师级的地位。他把探求古人类学的研究,通俗地概括为:“回答人是从哪里来?到底是神创造了人,还是劳动创造了人。这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哲学问题。”贾兰坡70岁以前基本上在野外搞调查发掘。88岁那年,他被选为美国世界探险中心会员,贾老说,我老得连小板凳也上不去了,怎么能和宇航员同称探险家呢?美国人说,你一生钻过三百多个山洞,没人能和你相比。贾兰坡在90多岁的高龄还在第一线带研究生,他常戏称“收个学生比养个儿子还难”。从学习上认真的指导到野外工作时对学生安全的时时挂心,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细心周到。贾兰坡的成长离不开裴文中等老前辈的培养,他深知好的老师和前辈能给年轻人带来什么。他说,我要为年轻人抬轿子,我要拉他们一把。贾老曾经写道:幸而世界上世世代代有这么一批“傻人”,愿为追求真理而奋斗终生。在真理面前,他们每有所得就笑逐颜开,一无所获又愁容满面。我们相信,一个人想要为人类作出一些有益的事,就无法摆脱这种苦乐相兼的境界。但是他们从来不气馁……我们的先辈是如此,我们是如此,一代一代下去也是如此。贾兰坡生前曾经说过“周口店是我的家”。他向单位和家人表示,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能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周口店。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裴文中先生和古人类学家杨钟健先生都已长眠在周口店龙骨山上。贾老早年就表示过身后要与两位前辈做伴,要栖守着自己奋斗过的地方。贾兰坡百年之后,祖国和人民了却了他生前的愿望。老人虽已驾鹤西去,但他的精神和信念将永远留守在龙骨山,遥盼着令他魂牵梦萦的“北京人”早日归来。 1998年秋天,以贾兰坡为首的中国著名科学家联名,在《光明日报》发出了这样一份呼吁:贾兰坡等院士的呼吁信:对于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来说,有这样一件事情始终不能忘怀: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和世界的几位杰出的科学家,根据一些当时很少有人相信的线索,在中国北京附近的周口店龙骨山上日复一日地苦苦寻找了多年,终于导致了一个伟大发现——“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诞生,而这一发现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是从猿变化而来的”这个在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事实,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现之前还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爪哇猿人”的发现都曾经被斥为奇谈怪论。但是,当“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以其空前丰富而完备的原始人生活遗迹展现于世人面前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清晰而无可辩驳了。或许可以这么说,从1929年12月2日第一具北京猿人头盖骨出土的那一刻起,人类真正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过去了。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一伟大发现中最珍贵的部分——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和在中国发现的其他重要灵长类化石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乱中下落不明了。数十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此痛心疾首,也不知有多少人为寻找化石丢失的线索尽了心力。随着世纪末的临近,随着多数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辞世或年逾古稀,我们寻找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希望也愈来愈急切。我们在想:这样一件发现于本世纪初的人类科学珍宝,在世纪中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遗失,而今天人类将告别这个世纪的时候,它们仍然不能重见天日。即使它们已经损毁于战火,我们也应该努力找到一个确切的下落。否则,我们又将如何面对后人?当年北京猿人化石的失踪涉及到战乱中多个国家的当事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重要的线索可能流失于民间。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关心此事的人士一直在查访有关的线索。但是他们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需要我们大家各尽所能,提供自己所知的线索和其他一切有用的支持,一起来帮助寻找。因此,我们想在这里向全世界所有热爱科学、进步的人们呼吁:在本世纪结束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也许这次寻找仍然没有结局,但无论如何,它都会为后人留下珍贵的线索和历史资料。并且它还会是一次我们人类进行自我教育、自我觉悟的过程,因为我们要寻找的不仅仅是这些化石本身,更重要的是要寻找人类的良知,寻找我们对科学、进步和全人类和平的信念。让我们行动起来,继续寻找“北京人”,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资深院士:贾兰坡 刘东生 张弥曼 秦馨菱 叶大年陈庆宣 孙殿卿 李廷栋 宋叔和 吴汝康郝诒纯 王鸿祯 杨遵仪 侯仁之
朱希祖,字逷先。先世系出吴郡,后一迁歙县,再迁婺源。清光绪九年(1879年),他生于尚胥里上水村。1905年,考取官费,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史学。与鲁迅等同受业于章太炎之门。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演讲三民主义,朱希祖经常前往听讲,于是欲用明季历史,阐扬民族大义。1909年,学成回国,担任嘉兴第二中学教员,并宣扬革命学说。辛亥革命时,他被推为海盐县知事,乡里安堵。1913年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集国语读音统一会,朱希祖奉派出席。会议代表们审核音素、采定字母时众说纷纭,久争不决。朱希祖独主张采古文纂籀经省之形为字母;既采其形,复符本音;凡声母四十二,韵母十二,介母三,名为“注音字母”。代表们对此决议通过,因此,朱希祖之名动京师,国立北京大学马上聘为预科教员,并兼清史馆编纂。后因清史馆总纂赵尔巽赞成袁世凯帝制,背叛民国,朱希祖遂愤而辞职。不久改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史学系主任,讲授中国史学概要、断代史及文学史。1919年,朱希祖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提倡白话文学,并鼓吹民主与科学等革命思潮。他以为历史学是一种社会科学,必须用科学方法从事研究。研究历史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科学。考证史事须以原始史料与实物为依据,决不可轻信坊间辗转复制的次等材料。他主持北大史学系时,把课程分为六系:(一)史学的基本科学,(二)史学的辅助科学,(三)史学史及史学原理等,(四)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五)专门史,(六)第一、第二外国语都是必修科。这种制度施行后,国内公私大学历史系,一致采用。从此以后,中国史学乃得跻于科学之林,而史学名家培养渐多。1922年5月,朱希祖主持明清档案整理会,开设陈列室,供学者研究。他指导北大史学系同学整理,办法是分为三步:首就档案的形式分类,区分年代;次则编号摘由;再次者则研究、考证,并分类统计。以整理就绪者,送入陈列室,供人参观,并在《北大日刊》公布其事由。他编有《内阁档案各衙门交收天启崇祯事迹清单》。朱希祖整理档案的办法为后来文献馆整理内阁大库、军机处、内务府、清史馆及刑部等档案所采用。1926年,朱希祖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及北京私立辅仁大学教授。1928年,他仍回北大为史学系主任,兼清华大学等教授,并于是年秋发起中国史学会于北平。1930年改就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次年,日本军人发动沈阳事变,东北沦陷,朱希祖深痛国难严重,重新研究南明史乘,以发扬民族精神。1932年,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电聘朱希祖为文史研究所主任。1934年春应聘为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兼古物委员会委员。讲学之余,赴南京郊外作古迹调查,撰写调查报告书,又撰《伪齐录辑补》、《伪楚录辑补》及《杨么事迹考》,寓古为今用之义。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南京中央大学奉命西迁。是年11月,朱希祖随校到了四川重庆。会教育部拟颁布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朱希祖以为历史学系课程,当以学习理论为主;就学理言,则目的有二:一为发现历史真相,除普通史和社会、政治、经济为必修课外,须以考古、地史、人类、人种、言语等学为必修课,而以各种国别史为选修课,更辅以社会史、经济史、专门史等科目;二为发现历史真理。除普通史如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为选修课外,还要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等辅之。抗日战争既起,朱希祖尝论“藉历史以说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主张政府当开馆修史。1940年2月国民政府接受朱希祖关于筹办档案管理总库和国史馆的提议,于重庆歌乐山设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并聘请朱希祖为总干事。3月,又简任他为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于是,朱希祖辞去中大历史系主任之职,并迁居歌乐山向家湾。后又因多病,遂辞史馆职务,专任考试院务。并从事著作,昼夜无间,而病势日剧。1944年7月5日卒,年仅66岁。朱希祖自主持北大史学系以来,即以新史学相倡导,于南朝梁氏及南明历史,改力最久而精深。他尝游历陕西、晋北、金陵、广州以及名山大川,访求遗文旧事,并旁通目录、版本、校雠金石、考古等学。曾拟编刊史学丛考,公开发表。“九·一八”事变后,尝恨民族败类在东北、华北、南京组织伪政权,又愤于日寇沿袭金人封建张邦昌、刘豫故技,因而勾稽两宋史料,撰《伪楚录辑补》六卷、《伪齐录校补》四卷、《伪齐国志长编》十六卷,揭发敌人奸谋,揭汉奸秽迹,以昭告国人,以明学以致用之旨。
生活在北京的“番薯人”
张光直在他早年生活自述中,把自己称为“番薯人”。 之所以叫番薯人,那是因为公元1895年,大清帝国与日本在黄海及刘公岛海战中失利,被迫将台湾岛割与日本。从此,台湾岛上的居民便成为“亚细亚的孤儿”。因为台湾岛的形状很像一个白薯,所以岛上两三千万的汉人常常称们自己为“番薯人”。 可张光直这个番薯人,却出生在北京。
16岁之前,张光直一直随着父亲张我军生活在旧北京。张光直的父亲张我军本是台湾台北县板桥乡一个贫穷的佃农家庭的孩子。后来只身北上读书、工作,曾任北京师大、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院校教师,直到台湾光复的1946年才回到故乡台湾。张我军是台湾第一位白话诗人,回到台湾后,张我军利用所工作的《台湾民报》,介绍大陆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新文学革命主张,对台湾的年轻一代产生很大影响。1925年12月28日,张我军把自己与妻子的曲折的矢志不渝的恋爱经历写成新诗集《乱都之恋》,自费出版,成为台湾岛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这本诗集出版之际,正是日本殖民主义在台湾实行严厉的思想钳制、推行“皇民化”文化、禁止汉语传习的时期。台湾人为了民族尊严,只好在各地创设诗社,以集会作诗为掩护,来延续民族文化的传递。不过,当年所有的诗作都是古风、律诗和绝句,到《乱都之恋》出版后,不少读书人才知道世间除了文言的旧体诗外,还有白话的新诗体,于是纷纷起而仿效,给宝岛的白话文运动以及诗体的解放,带来了一阵清新的涟漪。张我军还甘冒大不韪,毅然宣称:“台湾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指出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因此,张我军被人誉为“代表了台湾作家不畏强权的道德良心。”
由于从小生在、长在北京,张光直能说一口标准的漂亮的京片子,并且一生都对北京充满了浓浓的怀念情怀。在《番薯人的故事》里张光直用一种哀伤怀旧的笔调,写出了一个少年眼中的老北京:每天上下学走上高高的城墙,故都的景色一览无余;烧饼、麻花、炸油饼,又酸又苦的豆汁儿,蒜味钻鼻香的煎灌肠;热闹的厂甸,东西便宜,应有尽有。12岁的张光直曾用一块大洋买到一张宋拓的集王羲之字的《大唐圣教序》……除此之外,便是沦陷区人民的痛苦与反抗;作者的老师,回校时用毛巾包着几个馒头,这是一个礼拜的伙食——这个相当有名的数学家,最后倒卧冻死在风雪之中;早上在西单和东安两个市场上,报摊上竟然可以买到隔日的《解放报》、《晋察冀日报》,还有土纸印刷的《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等书刊,而每天冒着危险在冰冷的水里沿着护城河往来运送这些违禁报刊的,有一个正是作者小学的同班女同学,这个地下党员竟还是文化大汉奸管翼贤的女儿。
尤其让他记忆深刻的,是他在师大附小和附中读书的生活。由于品学兼优,从师大附小到师大附中、从附中初中到高中,张光直都是被保送的。尤其让他骄傲的是,师大附中是公认的北京最好的学校。从初一开始他结识了一生的好朋友温景昆。1946年家人回台定居时,他本来舍不得离开师大附中,但因为生病功课落了一大截,只好随家人返台。在《番薯的故事里》,张光直先生在回北京的生活时深情地提到:“不能忘记师大附中的校歌:附中,堂堂正正本校风,我们,莫忘了诚、爱、勤、勇。你是个神,愿人生大同。你是个海,涵真理无穷。附中,太阳照着你笑容,我们努力读书和做工。”
可以说,正是这故都文化的历史底蕴,孕育乃至影响了张光直的一生。他的一生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并为此竭心尽力,奔走于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各地,做出了无人能及的贡献。
从小就学习优异的张光直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初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跟随家人回到了台湾,在台湾著名的建国中学读高中。他的优秀学识迅速得到大家公认。受当时一位大陆去的魅力非凡的中文老师的影响,再加上在北京生活的那段背景,张光直的身上有着在那一代大陆青年身上可看见的时代赋予他们的热情、理想和勇气。1949年4月6日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发动了镇压台北教育新闻界的所谓共产党员的“四六事件”。大约有二十人被捕,张光直就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唯一的一位高中生,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一年时间。
张光直从监狱惊恐的阴影中走出,精神有所震动,但却不愤世嫉俗。一年的牢狱生活,张光直接触到各色各样的人。出来以后,他对“人之所以为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出来以后,他没有继续念书,在家里自己读点书,后来以同等学历考上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考这个系的基本原因就是想知道“人之所以为人”。
当然,张光直报考这个专业也深受两本书的影响。第一本书是由其父、著名的台湾文学作家张我军翻译的日本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书里讲述的人类进化史、石器时代对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948年时又读到裴文中先生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一书,裴先生在书中认为中国的考古学潜力无限,鼓励青年学生报考考古学专业,这使得张先生更加向往考古学。当时的考古专业是极其冷门的专业,但恰逢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台北,张光直为能受教于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等考古学精英而深感幸运。李济等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对他的确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4年,张光直从台大毕业,决心走出国门,到美国深造。他如愿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系的研究生。有两位老师对他的影响最大。一位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Hallam Movius,张光直跟随他掌握了传统的欧洲考古学的田野考古方法。另一位是在考古学上提出聚落形态研究方法的考古学家Gordon Willey。张光直对聚落形态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很感兴趣,积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生时便发表了关于美洲聚落考古的论文,为他后来写《古代中国考古学》这部重要著作奠定了基础。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聚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由Willey作指导,是将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用在中国史前史的成果。
张光直的确是一颗才华横溢、光芒四射的星星。他在哈佛做研究生时,著名的莫维斯教授看这个亚洲学生总是一言不发地坐在教室里,也不记半字笔记。而到了考试,这个学生却交了一份理论丰富、证据翔实的答卷,教授这才知道班里有一个天才青年。在还没得到博士学位之前,张光直就已经被文化人类学大家罗克教授称赞:“快要在我们系里得博士学位的张光直真了不起,十年来在人类学系里读博士的学生都比他不上。考博士口试时,他对各教授问他的各问题,答得那么应对如流,对理论对事实,都能把握得那么精深正确;不到半小时,大家都认为不须再问下去,于是都起来和他握手道贺。现在我们已经内定了聘他在本系做助教,今夏交博士论文后,即正式发聘书。”
此后的张光直可谓声名显赫。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6年,1977年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并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从事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1年至1984年兼人类学系系主任,1985年至1988年兼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并为哈佛赫德荪考古讲座教授,更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后二者皆为百年来华人之首任。
杰出的“架桥人”
张光直先生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史前考古,在学术上的贡献可谓硕果累累。他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中国文明的地位问题和史前时代东南沿海文化与台湾文化的关系几个问题的阐述中颇有建树。
1986年,张光直提出:中国文明的形成与西方文明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中国,有城市、有国家、有文字、有伟大艺术的新社会的产生,不是生产技术革命的结果,也不是贸易商业起飞的结果,而是通过政治秩序所造成的财富过度集中的结果。这条道路是非西方世界文明演进的共同道路,比如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大洋洲地区的文明等,都属于这条道路的例证。因此,社会科学应当根据体系完备、资料翔实的中国的历史经验重新思考人类社会进化规律的问题,应该修正现行世界史教科书中洗发膏本位主义的流行观念。
张光直的研究,一下子将中国考古学从中国历史的范畴中拉出来,置身于世界文化舞台当中,置身于文化演变的复杂过程当中。80年代以来,当中国考古学研究初现多元化色彩之时,张光直先生的研究不但成为这块多元色彩中最为醒目的一块,而且对这种多元化的来临起了相当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相互作用圈”理论,“亚美巫教底层学说”等,他介绍和倡导的聚落考古学等,不但赫然成为一家之言,也已经够成为当代中国考古学的最基本的理论方法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张光直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架桥人”。他把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介绍到了西方,又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带到了中国,为中西方考古学的接轨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张光直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几乎不被西方学界所承认,张先生可谓是改变这一局面的第一人。李润权先生在《张光直教授的学术成就》一文提到:“在西方世界,近40年来,张光直这个名字几乎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 我曾经听到中国的有些学者说,张光直的最大成就是及时地把中国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介绍给西方世界。”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有了改善。1975年,张光直参加美国古人类学家代表团,在离开北京近三十年后第一次访问北京。那时,与中国考古界同仁接触的机会仍非常受限制,在紧接着的1977年他又回国作了探亲旅游,1978年随汉代史研究代表团访华。但中国的政治状况渐渐好转,张光直利用各种资金资助,邀请中国大陆考古学家去美作学术访问,起先是短期交流,后来则作较长时间的地停留。开始这种机会仅限于年高资深的学者,80年代中期以后,年轻考古学家也陆续到哈佛做访问学者。张光直不知疲倦地担当着主人的角色,组织了无数次演讲、圆桌讨论、学术沙龙和宴会。自1980年开始,张光直还接纳中国大陆的研究生到哈佛攻读学位,他的一些学生在进入哈佛之前,也曾在中国接受过考古学训练。在80年代,他组织过两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1982年在夏威夷檀香山的“国际商文明学术会议”和1986年在弗吉尼亚的“古代中国和社会科学理论研讨会”。当时,外国学者还根本不允许在中国大陆参加考古学术会议,台湾学者也禁止前来大陆,大陆学者访问台湾更不可能。这两次会议为海峡两岸的学者以后的经常交往开创了良好的先例。80年代和90年代,张光直频频出访中国,有时一年几次。他对各地的大学作了短期访问,每次都受到热烈欢迎。张光直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中国大陆进行发掘,并为此奔走劳碌,甚至都已经争取到了基金,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没有得以实现。
《古代中国考古学》是在张光直先生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该书至今已经出版了四版,用英美人熟悉的语言全面介绍古代中国考古学,并把最新的研究成果传递给西方世界,成为目前世界大部分地区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和上古史的教材,影响极其深远,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贡献巨大。《古代中国考古学》《商文明》等书,已成为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圣经”,至今无人取代,被誉为是“比任何其他著作都更能把古代中国放在美国人类学意识的地图”上的对中国考古学的典范分析。
张光直先生一生最引以为豪的,莫过于在世界知名学府哈佛大学创立了中国考古专业,使哈佛大学成为西方学习中国考古学的中心。这是他毕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身患重病后非常放心不下的一件事。这样的担心不但“涉及到中国考古这个学科,而且关系到对古代中国的整体研究。”张先生还是台湾考古学的创立人,为台湾的史前考古做出了杰出贡献。1994年他经过多番努力,促成了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的成立,并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他主持的“台湾史前史研究计划”和“浊大计划”是两个影响深远的田野考古项目,对台湾的学术发展意义重大。
张光直先生一生培养多位英才,也影响了多位学者的学术道路。许倬云、余英时、徐苹芳、巫鸿、李零等学者们,都对先生勤奋严谨、大气磅礴的治学风格,谦虚礼貌、平易近人的待人态度,以及外冷内热、志存高远的气质性格有着深刻印象。张先生无论是在治学上还是组织办事能力上,都表现出了无穷的动力,感染和鼓励了众多学者。
1996年亚洲研究学会授予张光直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在授奖辞中这样写道:“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张光直教授为中国和东南亚考古的进步和发展鞠躬尽瘁、不遗余力。他的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杰出贡献,无人能望其项背。张光直教授几乎是独立一人担负了培养三代考古学研究生的重任,这些学生目前正执掌着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重要大学的教席……亚洲研究学会特此授予张光直教授最高的学术荣誉: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学会主席和各位成员与光临今天授奖仪式的诸位一道,宣布张教授为我们学会最杰出和最有成就的一员。”
在成就和名誉的背后,张光直先生常年饱受帕金森症的煎熬,1997年虽做了脑部胚胎移植疗法,健康却无起色。但他无言地忍受痛苦,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争取时间,仍然活跃在学术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1年1月3日,张光直先生在美国麻省因帕金森症病逝,享年七十岁。
然而,正如余英时先生在怀念张光直先生的文中所言:“他是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但是他的光和热已永远留在人间。”
张光直的往事略集视频
相关评论:
卫虾魏张光直的研究,一下子将中国考古学从中国历史的范畴中拉出来,置身于世界文化舞台当中,置身于文化演变的复杂过程当中。80年代以来,当中国考古学研究初现多元化色彩之时,张光直先生的研究不但成为这块多元色彩中最为醒目的一块,而且对这种多元化的来临起了相当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相互作用圈”理论,“亚美巫教底层...
卫虾魏黄仁宇的书一度很热,但我没有选择《万历十五年》,其中的一个顾虑是觉得公众未必都读出了该书的深意。这里选择黄仁宇的两本书,略近於随笔集,很像是对每个朝代、某些事件的素描,有些观察也颇能抓住要害。如果想要了解黄仁宇的整体史学观点,建议读一读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至于他的数目字管理,争议很大,误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