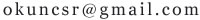汪曾祺 我的创作生涯
水墨世界
傍晚,夕阳滞留在天际
踏着黄昏的脚步徘徊渐远
树之林群山上的淡淡金辉
渐渐褪却,还原出墨绿色的翠
群鸟归来兮,叽叽喳喳
汇聚于树枝的殿堂
是今日最后一场盛宴后的感慨
还是睡眠前的又一次不休的争论
风的行者,万万千千,自虚空中
踏着叶的波浪而来,一摇一晃,似醉
扯下一张张夜色的幕,覆盖大地
持着一支支墨色的笔,涂抹山林
寂静,是这夜的音符
墨色,是这夜的真彩
下弦月,在天的一角
露出她微泛金色的幸福微笑
树的世界,寂寞无语
烈日炎炎似乎留下了些伤痛
让这夜的墨色抚慰曾经的辛劳
让这风的细语放松劳作的心灵
开一场夜的舞会
孤树对影,零星交错
翩然树叶如掌者,伸向天空
纤纤细叶婆娑者,纱衣灵动
更多的树是观众
他们多是树的巨人,如梧桐树、白桦树
沉稳而健壮,魅影幢幢
是饱经沧桑的顶天立地的长者
这夜的水墨世界中,隐隐地
有桃枝默默婀娜轻舞
有枇杷枝叶暗香浮动
有长袖如风漫卷丝丝清秀
变换了天与地
移幻了色与彩
唯有形影相随、明暗相伴
唯有香影漫漫飘自那叶的衣衫
夜的水墨世界啊
好似一场沉醉的夜会
迷离了明与晰,混沌了清与醒
淡化了时间,遗忘了朝代
乘一叶梦之舟,伴风而走
航行于夜的墨山黛水之间
沉醉于这暗影缠绵的画界
逍遥兮这混沌无极的天地
不想让你流泪
不想让你流泪
月色滑过你的肩膀
流走着眷恋的期望
银色的光芒闪过微凉
你的脸却是炙热滚烫
透明的泪水啊滚落到地上
发出刺耳的声响
染湿了地板
染湿了我的心
不想让你流泪
不想让你伤心
我只想你快乐
请记住我永远爱你
挚爱你的心永远不会放弃
因为我一直
深深的眷恋着你
星星照亮你的眼眸
流走着最甜美的笑容
微弱的光芒闪过温暖
那是你说要带我去远方
透明的希望啊滴落在地上
发出柔和的声响
染湿了地板
染湿了我的心
只想让你微笑
不想让你伤心
我只想你幸福
请记住我永远爱你
挚爱的心永远不会放弃
因为我一直
深深的眷恋着你
你知道吗
当你落泪的那一天
我就爱上了你
风月笔记
一
采撷朵朵桃花,抛撒在三月的
路上。一场邂逅,从桃香中缱绻开来
彼此不言不语,只是在清风中
嗅着缘分的气息
笑容开遍江南,烟雨从不干预
一场爱情的开始。于是把三叶草
织成一枚戒指,趁春色未尽
斜阳未落,替你戴上
一生的誓言
二
几米阳光透过帘隙,点亮一屋子
温馨。细听莺声燕语在梢头发酵
昨天酝酿了一坛子爱情,今天
准备将蜜月,酿上一个礼拜
你的呼吸在酒杯里久久沉埋
醉了一笺诗话,也醉了我的心
逐渐沉溺于你的柔情
我已——
难以自拔
独自在流星划过时
寻找天长地久,但至今
尚未发现蛛丝马迹
于是,在沉默中
饮下一抹星辉
三
日子轻描淡写,风花雪月从沧海
走到桑田。桃花纷纷扬扬
带着昨日辉煌,撒下
一地
破碎的笑
记忆遁入黑夜,脚步零零星星
或深或浅,并印下一叠
关于桃花的胶卷
笔记从三月开始,在一颦一笑中
层层展开。拈取一缕桃香
和着浅墨,记下了
一番风月
于是
爱情缩进云层
不再——
春暖花开……
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它以抒情的方式,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富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语言和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诗歌是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尚书·虞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与歌统称诗歌
我的创作生涯
汪曾祺
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的问题。我以为创作不是绝对不能教,问题是谁来教,用什么方法教。教创作的,最好本人是作家。教,不是主要靠老师讲,单是讲一些概论性的空道理,大概不行。主要是让学生去实践,去写,自己去体会。
我生在一个地主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从他那一科以后,就“废科举,改学堂”了。他对我比较喜欢。有一年暑假,他忽然高了兴,要亲自教我《论语》。我还在他手里“开”了“笔”,做过一些叫做“义”的文体的作文。“义”就是八股文的初步。我写的那些作文里有一篇我一直还记得:“孟子反不伐义。”孟子反随国君出战,兵败回城,他走在最后。事后别人给他摆功,他说:“非敢后也,马不前也。”为什么我对孟子反不伐其功留下深刻的印象呢?现在想起来,这一小段《论语》是一篇极短的小说:有人物,有情节,有对话。小说,或带有小说色彩的文章,是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并且,这篇极短的小说对我的品德的成长,是有影响的。小说,对人是有作用的。我在后面谈到文学功能的问题时还会提到。我的父亲是个很有艺术气质的人。他会画画,刻图章,拉胡琴,摆弄各种乐器,糊风筝。他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做“百脚”)是用胡琴的老弦放的。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人。如果说我对文学艺术有一点“灵气”,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来的遗传基因有点关系。我喜欢看我父亲画画。我喜欢“读”画帖。我家里有很多有正书局珂罗版影印的画帖,我就一本一本地反复地看。我从小喜欢石涛和恽南田,不喜欢仇十洲,也不喜欢王石谷。倪云林我当时还看不懂。我小时也“以画名”,一直想学画。高中毕业后,曾想投考当时在昆明的杭州美专。直到四十多岁,我还想彻底改行,到中央美术学院从头学画。我的喜欢看画,对我的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我把作画的手法融进了小说。有的评论家说我的小说有“画意”,这不是偶然的。我对画家的偏爱,也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影响。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一个人的成为作家,跟小时候所受的语文教育,跟所师事的语文教员很有关系。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教我们语文(当时叫做“国文”),都是高北溟先生。我有一篇小说《徙》,写的就是高先生。小说,当然会有虚构,但是基本上写的是高先生。高先生教国文,除了部定的课本外,自选讲义。我在《徙》里写他“所选的文章看来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是不错的。他很喜欢归有光,给我们讲了《先妣事略》《项脊轩志》。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讲到“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的时候充满感情的声调。有一年暑假,我每天上午到他家里学一篇古文,他给我讲的是“板桥家书”“板桥道情”。我的另一位国文老师是韦子廉先生。韦先生没有在学校里教过我。我的三姑父和他是朋友,一年暑假请他到家里来教我和我的一个表弟。韦先生是我们县里有名的书法家,写魏碑,他又是一个桐城派。韦先生让我每天写大字一页,写《多宝塔》。他教我们古文,全部是桐城派。我到现在还能背诵一些桐城派古文的片段。印象最深的是姚鼐的《登泰山记》。 “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崃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我当时就觉得写得非常的美。这几十篇桐城派古文,对我的文章的洗炼,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一九三八年,我们一家避难在乡下,住在一个小庙,就是我的小说《受戒》所写的庵子里。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数理化教科书外,所带的书只有两本,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沈从文选集》,我就反反复复地看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对我后来的写作,影响极大。
一九三九年,我考入西南联大的中国文学系,成了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沈先生在联大开了三门课,一门“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一门“创作实习”,一门“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是凤凰人,说话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小,简直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他讲课可以说是亳无系统。没有课本,也不发讲义。只是每星期让学生写一篇习作,第二星期上课时就学生的习作讲一些有关的问题。“创作实习”由学生随便写什么都可以,“各体文习作”有时会出一点题目。我记得他给我的上一班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写的散文很不错,都由沈先生介绍在报刊上发表了。他给我的下一班出过一个题目,这题目有点怪:《记一间屋子的空气》。我那一班他出过什么题目,我倒记不得了。沈先生的这种办法是有道理的,他说:“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现在有些初学写作的大学生,一上来就写很长的大作品,结果是不吸引人,不耐读,原因就是“零件”车得少了,基本功不够。沈先生讲创作,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写”。我们有的同学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感情要随时和人物贴得很紧,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不能离开人物,自己去抒情,发议论。作品里所写的景象,只是人物生活的环境。所写之景,既是作者眼中之景,也是人物眼中之景,是人物所能感受的,并且是浸透了他的哀乐的。环境,不能和人物游离,脱节。用沈先生的说法,是不能和人物“不相粘附”。他的这个意思,我后来把它称为“气氛即人物”。这句话有人觉得很怪,其实并不怪。作品的对话得是人物说得出的话,如李笠翁所说:“写一人即肖一人之口吻。”我们年轻时往往爱把对话写得很美,很深刻,有哲理,有诗意。我有一次写了这样一篇习作,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对话写得越平常,越简单,越好。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如果有两个人在火车站上尽说警句,旁边的人大概会觉得这二位有神经病。沈先生这句简单的话,我以为是富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沈先生教写作,用笔的时候比用口的时候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习作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比原作还长),或谈这篇作品,或由此生发开去,谈有关的创作问题。这些读后感都写得很精彩,集中在一起,会是一本很漂亮的文论集。可惜一篇也没有保存下来,都失散了。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个独到的办法。看了学生的习作,找了一些中国和外国作家用类似的方法写成的作品,让学生看,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我记得我写过一篇《灯下》(这可能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写个小店铺在上灯以后各种人物的言谈行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是所谓“散点透视”吧。沈先生就找了几篇这样写法的作品叫我看,包括他自己的《腐烂》。这样引导学生看作品,可以对比参照,触类旁通,是会收到很大效益,很实惠的。
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的问题。我以为创作不是绝对不能教,问题是谁来教,用什么方法教。教创作的,最好本人是作家。教,不是主要靠老师讲,单是讲一些概论性的空道理,大概不行。主要是让学生去实践,去写,自己去体会。沈先生把他的课程叫做“习作”“实习”,是有道理的。沈先生教创作的方法,我以为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方法。
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今年七十岁了,写作生涯整整经过了半个世纪,但是写作的数量很少。我的写作中断了几次。有人说我的写作经过了一个三级跳,可以这样说。四十年代写了一些。六十年代初写了一些。当中“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样板戏”。八十年代后小说、散文写得比较多。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开玩笑说“汪伯伯是大器晚成”。我绝非“大器”,——我从不写大作品,“晚成”倒是真的。文学史上像这样的例子不是很多。不少人到六十岁就封笔了,我却又重新开始了。是什么原因,这里不去说它。
有一位评论家说我是唯美的作家。“唯美”本不是属于“坏话类”的词,但在中国的名声却不大好。这位评论家的意思无非是说我缺乏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我的作品没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我于此别有说焉。教育作用有多种层次。有的是直接的。比如看了《白毛女》,义愤填膺,当场报名参军打鬼子。也有的是比较间接的。一个作品写得比较生动,总会对读者的思想感情、品德情操产生这样那样的作用。比如读了孟子反不伐,我不会立刻变得谦虚起来,但总会觉得这是高尚的。作品对读者的影响常常是潜在的,过程很复杂,是所谓“潜移默化”。正如杜甫诗《春雨》中所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曾经说过,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一读点我的作品。我对生活,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人类是有前途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愿意把这些朴素的信念传达给人。我没有那么多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我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我认为中国也不具备产生那样的作品的条件。
一个当代作家的思想总会跟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有些血缘关系。但是作家的思想是一个复合体,不会专宗哪一种传统思想。一个人如果相信禅宗佛学,那他就出家当和尚去得了,不必当作家。废名晚年就是信佛的,虽然他没有出家。有人说我受了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些。我年轻时很爱读《庄子》。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一些。我觉得孔子是个通人情,有性格的人,他是个诗人。我不明白,为什么研究孔子思想的人,不把他和“删诗”联系起来。他编选了一本抒情诗的总集——《诗经》,为什么?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的这种潇洒自然的生活态度是很美的。这倒有点近乎庄子的思想。我很喜欢宋儒的一些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 “生意满”,故可欣喜,“苦人多”,应该同情。我的小说所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小儿女”,我对他们充满了温爱,充满了同情。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
前几年,北京市作协举行了一次我的作品的讨论会,我在会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题目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为什么说“回到”呢?因为我在年轻时曾经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台湾家杂志在转载我的小说的前言中,说我是中国最早使用意识流的作家。不是这样。在我以前,废名、林徽因都曾用过意识流方法写过小说。不过我在二十多岁时的确有意识地运用了意识流。我的小说集第一篇《复仇》和台湾出版的《茱萸集》的第一篇《小学校的钟声》,都可以看出明显的意识流的痕迹。后来为什么改变原先的写法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我自己的原因。简单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觉得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不会是一回事。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学,绝不会像西方文学一样,除非你侨居外国多年,用外国话思维。我写的是中国事,用的是中国话,就不能不接受中国传统,同时也就不能不带有现实主义色彩。语言,是民族传统的最根本的东西。不精通本民族的语言,就写不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文学。但是我所说的民族传统是不排除任何外来影响的传统,我所说的现实主义是能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比如现代派、意识流,本身并不是坏东西。我后来不是完全排除了这些东西。我写的小说《求雨》,写望儿的父母盼雨。他们的眼睛是蓝的,求雨的望儿的眼睛是蓝的,看着求雨的孩子的过路人的眼睛也是蓝的,这就有点现代派的味道。《大淖记事》写巧云被奸污后错错落落,飘飘忽忽的思想,也还是意识流。不过,我把这些融入了平常的叙述语言之中了,不使它显得“硌生”。我主张纳外来于传统,融奇崛于平淡,以俗为雅,以故为新。
关于写作艺术,今天不想多谈,我也还没有认真想过,只谈一点: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仅是所谓“载体”,它是作品的本体。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谁也没有创造过一句全新的语言。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我们的语言都是有来历的,都是从前人的语言里继承下来,或经过脱胎、翻改。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的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就会更多。毛主席写给柳亚子的诗“落花时节读华章”,“落花时节”不只是落花的时节,这是从杜甫《江南逢李龟年》里化用出来的。杜甫的原诗是: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落花时节”就包含了久别重逢的意思。
语言要有暗示性,就是要使读者感受到字面上所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即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写的是个新嫁娘: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诗里并没有写出这个新嫁娘长得怎么样,但是宋人诗话里就指出,这一定是一个绝色的美女。因为字里行间已经暗示出来了。语言要能引起人的联想,可以让人想见出许多东西。因此,不要把可以不写的东西都写出来,那样读者就没有想象余地了。
语言是流动的。
有一位评论家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没有什么,放在起,就有点味道。我想谁的语言都是这样,每一句都是平常普通的话,问题就在“放在一起”,语言的美不在每一个字,每一句,而在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他的字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觉得怎么美,甚至不很平整,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文学语言也是这样,句与句,要互相映带,互相顾盼。一篇作品的语言是有一个整体,是有内在联系的。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语言是活的。中国人喜欢用流水比喻行文。苏东坡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吾文如万斛泉源”。说一个人的文章写得很顺,不疙里疙瘩的,叫做“流畅”。写一个作品最好全篇想好,至少把每一段想好,不要写一句想一句。那样文气不容易贯通,不会流畅。
本文来源:《汪曾祺经典》,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汪曾祺 我的创作生涯视频
相关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