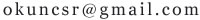急求一篇老舍的文章 要好词多的
春天好似不管人间有什么悲痛,又带着它的温暖与香色来到北平。地上与河里的冰很快的都化开,从河边与墙根都露出细的绿苗来。柳条上缀起鹅黄的碎点,大雁在空中排开队伍,长声的呼应着。一切都有了生意,只有北平的人还冻结在冰里。
苦了小顺儿和妞子。这本是可以买几个模子,磕泥饽饽的好时候。用黄土泥磕好了泥人儿,泥饼儿,都放在小凳上,而后再从墙根采来叶儿还卷着的香草,摆在泥人儿的前面,就可以唱了呀:“泥泥饽饽,泥泥人儿耶,老头儿喝酒,不让人儿耶!”这该是多么得意的事呀!可是,妈妈不给钱买模子,而当挖到了香草以后,唱着“香香蒿子,辣辣罐儿耶”的时候,父亲也总是不高兴的说:“别嚷!别嚷!”
他们不晓得妈妈近来为什么那样吝啬,连磕泥饽饽的模子也不给买。爸爸就更奇怪,老那么横虎子似的,说话就瞪眼。太爷爷本是他们的“救主”,可是近来他老人家也仿佛变了样子。在以前,每逢柳树发了绿的时候,他必定带着他们到护国寺去买赤包儿秧子,葫芦秧子,和什么小盆的“开不够”与各种花仔儿。今年,他连萝卜头,白菜脑袋,都没有种,更不用说是买花秧去了。
爷爷不常回来,而且每次回来,都忘记给他们带点吃食。这时候不是正卖豌豆黄,爱窝窝,玫瑰枣儿,柿饼子,和天津萝卜么?怎么爷爷总说街上什么零吃也没有卖的呢?小顺儿告诉妹妹:“爷爷准是爱说瞎话!”
祖母还是待他们很好,不过,她老是闹病,哼哼唧唧的不高兴。她常常念叨三叔,盼望他早早回来,可是当小顺儿自告奋勇,要去找三叔的时候,她又不准。小顺儿以为只要祖母准他去,他必定能把三叔找回来。他有把握!妞子也很想念三叔,也愿意陪着哥哥去找他。因为这个,他们小兄妹俩还常拌嘴。小顺儿说:“妞妞,你不能去!你不认识路!”妞子否认她不识路:“我连四牌楼,都认识!”
一家子里,只有二叔满面红光的怪精神。可是,他也不是怎么老不回来。他只在新年的时候来过一次,大模大样的给太爷爷和祖母磕了头就走了,连一斤杂拌儿也没给他们俩买来。所以他们俩拒绝了给他磕头拜年,妈妈还直要打他们;臭二叔!胖二婶根本没有来过,大概是,他们猜想,肉太多了,走不动的缘故。
最让他们羡慕的是冠家。看人家多么会过年!当妈妈不留神的时候,他们俩便偷偷的溜出去,在门口看热闹。哎呀,冠家来了多少漂亮的姑娘呀!每一个都打扮得那么花哨好看,小妞子都看呆了,嘴张着,半天也闭不上!她们不但穿得花哨,头和脸都打扮得漂亮,她们也都非常的活泼,大声的说着笑着,一点也不象妈妈那么愁眉苦眼的。她们到冠家来,手中都必拿着点礼物。小顺儿把食指含在口中,连连的吸气。小妞子“一、二、三,”的数着;她心中最大的数字是“十二”,一会儿她就数到了“十二个瓶子!十二包点心!十二个盒子!”她不由的发表了意见:“他们过年,有多少好吃的呀!”
他们还看见一次,他们的胖婶子也拿着礼物到冠家去。他们最初以为她是给他们买来的好吃食,而跑过去叫她,她可是一声也没出便走进冠家去。因此,他们既羡慕冠家,也恨冠家——冠家夺去他们的好吃食。他们回家报告给妈妈:敢情胖婶子并不是胖得走不动,而是故意的不来看他们。妈妈低声的嘱咐他们,千万别对祖母和太爷爷说。他们不晓得这是为了什么,而只觉得妈妈太奇怪;难道胖二婶不是他们家的人么?难道她已经算是冠家的人了么?但是,妈妈的话是不好违抗的,他们只好把这件气人的事存在心里。小顺儿告诉妹妹:“咱们得听妈妈的话哟!”说完他象小大人似的点了点头,仿佛增长了学问似的。
是的,小顺儿确是长了学问。你看,家中的大人们虽然不乐意听冠家的事,可是他们老嘀嘀咕咕的讲论钱家。钱家,他由大人的口中听到,已然只剩了一所空房子,钱少奶奶回了娘家,那位好养花的老头儿忽然不见了。他上哪儿去了呢?没有人知道。太爷爷没事儿就和爸爸嘀咕这回事。有一回,太爷爷居然为这个事而落了眼泪。小顺儿忙着躲开,大人们的泪是不喜欢教小孩子看见的。妈妈的泪不是每每落在厨房的炉子上么? 更教小顺儿心里跳动而不敢说什么的事,是,听说钱家的空房子已被冠先生租了去,预备再租给日本人。日本人还没有搬了来,房屋可是正在修理——把窗子改矮,地上换木板好摆日本的“榻榻米”。小顺儿很想到一号去看看,又怕碰上日本人。他只好和了些黄土泥,教妹妹当泥瓦匠,建造小房子。他自己作监工的。无论妹妹把窗子盖得多么矮,他总要挑剔:“还太高!还太高!”他捏了个很小的泥人,也就有半寸高吧。“你看看,妹,日本人是矮子,只有这么高呀!”
这个游戏又被妈妈禁止了。妈妈仿佛以为日本人不但不是那么矮,而且似乎还很可怕;她为将要和日本人作邻居,愁得什么似的。小顺儿看妈妈的神气不对,不便多问;他只命令妹妹把小泥屋子毁掉,他也把那个不到半寸高的泥人揉成了个小球,扔在门外。
最使他们俩和全家伤心的是常二爷在城门洞里被日本人打了一顿,而且在瓮圈儿里罚跪。
常二爷的生活是最有规律的,而且这规律是保持得那么久,倒好像他是大自然的一个钟摆,老那么有规律的摆动,永远不倦怠与停顿。因此,他虽然已经六十多岁,可是他自己似乎倒不觉得老迈;他的年纪仿佛专为给别人看的,象一座大钟那样给人们报告时间。因此,虽然他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一升火就象砖窑似的屋子,穿的是破旧的衣裳,可是他,自青年到老年,老那么活泼结实,直象刚挖出来的一个红萝卜,虽然带着泥土,而鲜伶伶的可爱。
每到元旦,他在夜半就迎了神,祭了祖,而后吃不知多少真正小磨香油拌的素馅饺子——他的那点猪肉必须留到大年初二祭完财神,才作一顿元宝汤的。吃过了素馅饺子,他必须熬一通夜。他不赌钱,也没有别的事情,但是他必须熬夜,为是教灶上老有火亮,贴在壁上的灶王爷面前老烧着一线高香。这是他的宗教。他并不信灶王爷与财神爷真有什么灵应,但是他愿屋中有点光亮与温暖。他买不起鞭炮,与成斤的大红烛,他只用一线高香与灶中的柴炭,迎接新年,希望新年与他的心地全是光明的。后半夜,他发困的时候,他会出去看一看天上的星;经凉风儿一吹,他便又有了精神。进来,他抓一把专为过年预备的铁蚕豆,把它们嚼得嘣嘣的响。他并不一定爱吃那些豆子,可是真满意自己的牙齿。
天一亮,他勒一勒腰带,顺着小道儿去“逛”大钟寺。没有人这么早来逛庙,他自己也并不希望看见什么豆汁摊子,大糖葫芦,沙雁,风车与那些红男绿女。他只是为走这么几里地,看一眼那座古寺;只要那座庙还存在,世界仿佛就并没改了样,而他感到安全。 看见了庙门,他便折回来,沿路去向亲戚朋友拜年。到十点钟左右,他回到家,吃点东西,便睡一个大觉。大年初二,很早的祭了财神,吃两三大碗馄饨,他便进城去拜年,祁家必是头一家。
今年,他可是并没有到大钟寺去,也没到城里来拜年。他的世界变了,变得一点头脑也摸不着。夜里,远处老有枪声,有时候还打炮。他不知道是谁打谁,而心里老放不下去。象受了惊吓的小儿似的,睡着睡着他就猛的一下子吓醒。有的时候,他的和邻居的狗都拚命的叫,叫得使人心里发颤。第二天,有人告诉他:夜里又过兵来着!什么兵?是我们的,还是敌人的?没人知道。
假若夜里睡不消停,白天他心里也不踏实。谣言很多。尽管他的门前是那么安静,可是只要过来一辆大车或一个行人,便带来一片谣言。有的说北苑来了多少敌兵,有的说西苑正修飞机场,有的说敌兵要抓几千名夫子,有的说沿着他门前的大道要修公路。抓夫?他的儿子正年轻力壮啊!他得设法把儿子藏起去。修公路
?他的几亩田正在大道边上;不要多,只占去他二亩,他就受不了!他决定不能离开家门一步,他须黑天白日盯着他的儿子与田地! 还有人说:日本人在西苑西北屠了两三个村子,因为那里窝藏着我们的游击队。这,常二爷想,不能是谣言;半夜里的枪声炮响不都是在西北么?他愿意相信我们还有游击队,敢和日本鬼子拼命。同时,他又怕自己的村子也教敌人给屠了。想想看吧,德胜门关厢的监狱不是被我们的游击队给砸开了么?他的家离德胜门也不过七八里路呀!屠村子是可能的!
他不但听见,也亲眼看见了:顺着大道,有许多人从西北往城里去,他们都扶老携幼的,挑着或背着行李。他打听明白:这些人起码都是小康之家,家中有房子有地。他们把地象白给似的卖出去,放弃了房子,搬到城里去住。他们怕屠杀。这些人也告诉他:日本人将来不要地税,而是要粮食,连稻草与麦秆儿全要。你种多少地,收多少粮,日本人都派人来监视;你收粮,他拿走!你不种,他照样的要!你不交,他治死你!(第35章)
[编辑本段]■林汝为版《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
电视剧《四世同堂》,共28集,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录制。1985年8月16日至9月9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根据老舍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林汝为(执笔)、李翔、牛星丽编剧。林汝为总导演。史可夫、蔡洪德、史宪富导演,梁世龙、邢培修、王晓辉摄像。创作集体获广播电影电视部授予的特别奖,作品获第六届(1985年度)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连续剧特别奖。该剧较忠实地再现了原著的思想内蕴和悲剧意识,人物形象丰满、生动、深刻。北平小羊圈胡同四世同堂的祁老太爷一家和他的街坊们,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和侵略者占领时期表现出来的双重性格,即不甘屈服的民族气节和封建思想的禁锢下封闭、愚昧、妥协、敷衍、无聊、自私等社会心理中的陈腐部分引人深思。时逢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因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文学性引起强烈反响,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话题。老舍先生的原著也因此而重现光彩。
是《我的母亲》,但具体写于那一年就不知道了,原文如下:
老舍《我的母亲》
正文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结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急求一篇老舍的文章 要好词多的视频
相关评论: